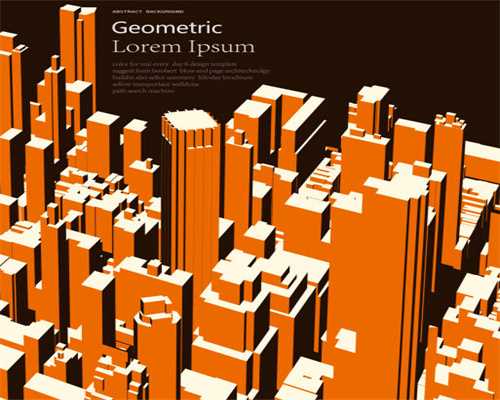我是莫府养了十几年的假千金。
真千金回来后,我成了偷走她人生的小偷。
爹说我改不了骨子里的劣根性,娘质问我有什么脸好好活着,哥哥踩断了我弹琴的手,要将我赶出莫家。
后来我替真千金挡了一剑,快要死了。
他们却都来求我好好活下去。
1
我替莫宛溪挡了一剑,快要死了。
她那般娇弱,却硬是背着我跑了二里地,找来城里最好的郎中,要他为我医治。
她紧紧抓着我的手,像是鼓励我,又像是在鼓励她自己。
“莫清,我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。”
我有没有事不知道,一年未见,她弱不禁风的身子骨倒是养好了很多。
莫宛溪刚被接回莫家时,浑身是伤,瘦得皮包骨头,像一株娇弱不堪的小白菊,我见犹怜。
我娘心疼极了,抱着她直流泪:“我的宛溪儿受苦了。”
听了这话,我很是无地自容。
她是受苦了,我却替她享了福。
我在莫家锦衣玉食,无忧无虑地长大。
可莫宛溪呢。
她从小生活在忻州的贫民窟,吃了不少苦,还差点流落青楼。
哥哥在忻州遇见她时,她刚从青楼逃出来,被五六个打手追上,打得半死。
是哥哥救了她。
看见她那张和娘八分相似的脸后,哥哥惊讶极了。
一个荒诞的猜想,在他脑海中浮现。
为了验证这个猜测,哥哥带着莫宛溪回到了京城。
爹娘看到她的长相,再看看长得既不像爹也不像娘的我,心中有了答案。
再然后,顺藤摸瓜往下一查,真相很快便水落石出。
我亲娘曾是莫家的婢女。
当年她和我娘同时生产,诞下女儿。
我们两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,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莫家千金,是在爱和期待中出生的,她尚在襁褓中,就拥有了满满一屋子金银珠宝,七八个乳娘围着她转。
而我,生父不详,偷偷摸摸出生,亲娘处境窘困,我连一口米汤都难喝上,能不能活过这个冬天都成问题。
我亲娘看着襁褓中熟睡的两个孩子,心生歹念,鬼迷心窍,竟来了个偷天换日。
我成了莫府千金莫清,而真正的莫家千金,成了莫府逃奴莫春娘的私生女儿,莫宛溪。
我亲娘害怕事情败露,连夜带着莫宛溪逃到了忻州。
做了亏心事的人,整日惶恐,躲在贫民窟,不敢在外抛头露面。
莫宛溪五岁那年,她染上重病,很快就撒手人寰。
倒是可怜了莫宛溪,小小年纪便成了孤女,吃百家饭长大,有惊无险地活到了十三岁。
她本是枝头的凤凰,却因我亲娘的一念之差,人生天翻地覆,明珠蒙尘,坠入泥潭。
而我,这颗被偷藏进凤凰窝的麻雀蛋,安稳地享受了十三年富贵人生。
可是啊,偷来的东西,成不了真,总有一天要还回去。
我明明已经把所有属于她的东西,全都拱手归还。
却仍旧无法缓解内心无尽的苦楚与孤寂。
是以,当那刺客提剑刺向莫宛溪时,我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她身前。
就这样结束吧。
我活着时,所有人都有意无意地告诉我,我欠莫宛溪的,我得弥补她。
如今我要死了,那些亏欠,是不是就该一笔勾销了?
无端背上这么大一笔债,真的好累好累。
好想立刻结束。
但莫宛溪抓着我的手,一个劲地叫我名字,让我坚持住。
我不。我不要再坚持了。
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挣脱她的手。
莫宛溪,这条命还你。
往后,我再也不欠你了。
2
我死了,但没完全死。
我的灵魂飘在屋内,无法离开。
我的肉体躺在榻上,残存一息。
那一剑将我刺了个对穿,我本就必死无疑。
莫宛溪请来了忻州最好的大夫,用千年雪参吊住了我一口气。
等那口气没了,我就彻彻底底死了。
莫宛溪把身上所有值钱的金银首饰都给了大夫,求他救我。
大夫无能为力地摇头叹气:“这一剑伤及命脉,华佗在世也救不回来,吊住她最后一口气,已是我的极限。”
莫宛溪握紧我的手,似是鼓舞般:“莫清,你撑住,我已经写信告诉爹娘和哥哥了,他们很快就来。”
我觉得没必要,反正他们也不会来,还不如现在就给我收尸。
爹娘和哥哥恨我,我知道的。
他们有多心疼莫宛溪,就有多恨我。
莫宛溪回归莫家那天,我娘第一次用审视的目光,冷冰冰地看着我。
“既然你的亲人都不在了,那你便留在莫府,给宛溪做个伴吧,但你要记住你的身份,欠宛溪的,你得还。”
那时我天真地以为,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,只是多了个玩伴而已。
直到我娘让我搬出清光苑。
清光苑四季都有花开,每一株都是我亲手栽种。
我明白,清光苑已经属于莫宛溪,但这里的一草一木,都承载着我的回忆。
我舍不得那些花草树木,还想再争取:“我可以住厢房,住下人房,别让我离开清光苑,求您。”
我娘回避了我祈求的眼神,漠然道:“宛溪看到你,会不开心的。”
我好想告诉娘,如果没有清光苑花花草草的陪伴,我也会不开心。
但我知道,我是假千金,她是真千金,所以,她的开心比我的开心重要。
于是,我搬到了清冷破败的偏院。
后来,我又被勒令不许随意出现在前厅,也不许穿着华丽的衣裙,更不许在莫宛溪面前展示琴棋书画——虽然我也只精通一个琴。
这些我都无所谓了,我唯一在意的是,厨房送的饭总是隔夜的,有时连隔夜饭都没有。
库房送来的用品也都劣质,尤其是冬天供应的碳,烧起来浓烟滚滚,能把好人呛出肺病。
我不是没想过告状诉苦。
我去找爹,爹说我太娇气,这点苦都不能吃。
可他忘了,很久以前,他亲口说过,有他在,他的小阿清这辈子都不用吃苦。
没人告诉过我,原来大人说话也会不算话。
那个听见我吸溜鼻涕,都会紧张得请来七八个郎中的爹爹,变成说谎的小鸟飞走啦。
如今我咳得满脸通红,他也只是淡淡地说:“你生病了,记得避着点宛溪,别把病气过给她。”
我去找娘,娘看我的眼神比爹更冷:“宛溪从前过得比你苦多了,你至少还有饭吃,宛溪可是饱一顿饿一顿捱过来的,更别说碳火了,你知道贫民窟每年会冻死多少人吗?”
哦,虽然我不知道贫民窟每年会冻死多少人。
但我知道,我娘这番话,真是冻得我浑身发冷。
因为这些苦都是莫宛溪曾受过的,所以我也得受着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
我娘是当家主母,后宅的事,是逃不过她的眼睛的。
如果没有她的默许,下人们吃了熊心豹子胆也不敢如此苛待我。
她这是在替莫宛溪出气。
她怪我让莫宛溪吃了十三年的苦。
就连从前最疼我的哥哥,也跟变了个人一样,我的苦水还没倒完,他就失望地看着我。
“莫清,你怎么能这么自私?你知道我找到宛溪时,她遭遇了什么吗?她差点被人玷污,差点被青楼的打手打死。”
“她才十三岁,如果不是你,宛溪怎么会遇到这些事,莫家愿意收留你,已经顾念了往日的情分,你要是还有点良心,就别再给人添麻烦了。”
我那时也才十三岁。
很多事我都不懂。
不懂曾经爱我疼我的家人,为什么一夕之间变得如此冷漠。
不懂这世上有因果报应,我亲娘犯下的罪孽,终究要回馈到我身上。
我还处在容易委屈的年龄,却被所有人告知,我没资格委屈。
没有人记得,我曾经也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,孩子是不懂什么是对错的,但能轻易地感知到爱和不爱。
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,但清清楚楚地知道,爹娘和哥哥不爱我了。
然后,从某天开始,厨房不再送来馊饭,夏天的冰不再短缺,秋天的瓜果不再变质,最重要的是,偏院终于烧上了无烟碳,我的咳疾彻底痊愈。
起初我以为是爹娘回心转意,念起了我的好。
直到有天,我从库房路过,看见莫宛溪指挥着几个下人,把上好的无烟碳装进小筐里。
“这些,全都给莫清送去,别让我发现你们私自克扣。”
有个小奴小声提醒:“小姐,您把自己的份例分了一半出去。”
“清光苑暖和,用不着那么……”莫宛溪解释了一半又板起脸,“你管那么多作甚,赶快送过去!”
我默默垂眸。
莫宛溪,你为什么这么好?
你越是这样,我越觉得亏欠你。
3
我没想到,我爹竟然会来。
他站在门口,踟蹰着不敢进来。
喃喃自语道:“那么活蹦乱跳的人,怎么可能要死了。”
他隔了老远,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摇着头往外走。
“不会的,宛溪,你一定是搞错了,这不是莫清,只是个和她长得像的人。”
莫宛溪淡淡道:“您如果真是这么想的,就不会快马加鞭从京城赶来了,两天的路程,您只用了一天半,马都跑死了三匹……既然来了,就进去看看她吧。”
我爹背着身站了许久。
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,他的背影看着好悲凉,仿佛一瞬间苍老了好多。
他真的站了好久好久,久到我以为他会就此离开时,他才转过身,慢慢挪到我床前。
“这是莫清?”他盯着我看了半晌,讷讷道:“怎么瘦了这么多,都认不出来了。”
“昭儿不是说,你在忻州过得挺好的吗?”
莫昭是我哥哥,哦,不对,他现在是莫宛溪的哥哥。
我离开京城后,他的确来过忻州,还发疯似的大闹了一场。
我们算是不欢而散。
我没想到,他回京后,还向爹提起过我,不过看样子,他没说实话。
我在忻州,过得挺好的?
也算是吧,毕竟莫宛溪过了十三年这样的生活。
怎么不算好呢?
我住在莫宛溪曾生活过的贫民窟。
那里四季不见天光,阴冷潮湿,街头巷尾充斥着腐朽的味道——是饿死的猫狗或人散发出的味道。
那里的屋顶没有瓦片,只有茅草,用几块石头可怜地压着,若是遇到大风天,整个屋顶都要被掀翻,挡不住风,更挡不住雨。
这就是莫宛溪长大的地方。
我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。
白天睡觉,晚上发呆。
偶尔去后面的山林里觅食,但大部分时间都饥肠辘辘。
我也想知道,饱一顿饿一顿是怎么捱过来的。
没想到,日子真就这么浑浑噩噩捱过去了。
我才捱了一年,莫宛溪可是捱了十三年。
我爹小心翼翼地拉起我的手,看着我空荡荡的手腕,出了会儿神。
我知道,他大概是想到那串红豆手链了。
他亲手做的那串手链。
莫宛溪刚被接回来时,受了重伤,身体很虚弱。
某个雨夜,她高烧不退,爹娘和哥哥都急坏了。
我想为她做点什么,便熬了药粥端给她。
路上恰好遇见急匆匆赶去清光苑的爹。
我笑着上前:“爹爹,我给宛溪熬了……”
话未说完,我就被一把推开。
“让开。”
雨天路滑,我重心不稳,摔进泥坑,装着药粥的瓷盅摔得四分五裂,滚烫的粥洒得我满手都是,瓷片也扎进我的肉里。
我刚想喊疼,就看见红豆手链啪的断了。
红豆噼里啪啦,滚落得到处都是。
我连疼都忘了,怔怔地说:“爹,我的红豆手链断了。”
我爹闻言转过头,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:“宛溪都病成那样了,你还把心思放在这些处心积虑的算计上,莫清,你太让我失望了!”
我起初没懂他的意思,在冷雨里想了好久才明白。
原来,我给莫宛溪熬粥,在他看来,是处心积虑的算计。
我明明只是想要弥补莫宛溪。
我什么都不做,他们说我铁石心肠,没有良心。
可我一旦做点什么,他们又觉得我处心积虑,满心算计。
我想不通,一个人罪孽到底有多深重,才会做什么都是错。
我甚至怀疑,是不是我往莫宛溪面前一站,什么都不说,什么都不做,也是一种错?
那天我在滂沱大雨中找了好久,只找到十八颗红豆,剩下两颗怎么也找不到了。
连路过的下人都劝我放弃:“小姐,什么东西那么重要?找不到就别找了。”
或许也没那么重要,但那是我曾经拥有,现在失去的东西。
不只是那两颗红豆。
我曾经拥有它们,可我再也找不到了。
4
第二天,我也发起了高烧。
我好想解释,却又好无力。
最后只得恹恹地说:“爹,我的红豆手链断了。”
我爹似乎这才想起那串红豆手链的来历,怔愣片刻,皱起眉头:“都什么时候了,你还惦记着劳什子破手链,真是病得不轻!”
那才不是什么破手链。
二十颗红豆,都是爹亲手抛光打磨的,又亲手穿成手串,亲手给我戴上。
他说:“每颗红豆,都代表着爹对阿清的期许和祈福,希望爹的小阿清平平安安,一生幸福快乐。”
那不是破手链。
是被遗忘的爱和期许。
爹爹忘了,可我还记得。
但只有我一个人记得,那些爱和期许,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。
我一把火烧掉了被我捡回来的红豆。
从前我以为,这些红豆是我曾经拥有爱的证明。
可我现在才明白,不是。
它们是欺骗,是假象,是那些随口应下的承诺。
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,我曾拥有的一切是假的,全都是假的。
莫宛溪是在爱和期待中出生的,但我不是。
我是不被爱的人。
我这样的人,就应该悄无声息地死去,掀不起一点水花。
可为什么,我真的快死时,爹的眼里竟然隐隐有泪光?
他声音都在颤抖:“阿清,爹总觉得,这些年亏欠了宛溪,所以要尽心尽力弥补她,爹不敢对你好,是怕宛溪看见了心里难受。”
“你是爹看着长大的孩子,从那么小的雪白团子,长成玉雪可爱的小丫头,又从小丫头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,爹怎么会不爱你。”
“阿清,爹求求你,活下来,爹再给你串红豆手串”
原来爹全都记得。
我还以为,世上只剩我一个人,苦守着那些回忆。
他说他是爱我的。
可是,太迟了爹爹。
从前我贪心地想要一点爱,用一身伤也没能换来。
现在我不再需要了。
我快死了,爱也救不了我。
5
我娘不相信我会这么轻易死去。
她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质疑:“莫清真的快死了?该不会是又在要什么花招,想要吸引注意吧?”
莫宛溪听得直皱眉:“娘,莫清在您心里,就这么不堪吗?”
我娘一愣,看了看神情悲悯的莫宛溪,又看了看面色颓然的我爹,最后才看向我。
她终于确认,我是真的快死了。
我娘沉默了一会儿,来到床边坐下。
她说了句和我爹一样的话:“怎么瘦成这样?”
我爹说:“阿清从小就挑食”
说到一半,我爹顿住,没再往下说,眼里隐隐有泪。
我娘也红了眼眶,表情愧疚。
他们大概都想到了,我胃不好,从小就挑食,还总是胃疼。
可他们为了给莫宛溪出气,纵容厨房给我送隔夜饭。
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那些见风使舵的下人只会变本加厉。
我为此吃了不少苦头。
刚开始我还会使小性子,后来我发现,不会再有人在意我的小情绪了,哭也没用,闹也没用,没人会再耐心哄我。
于是我受了委屈,也不再和任何人说,只一个人默默承受
没人疼的小孩,只能在夜里独自消化坏情绪。
我娘小心翼翼掀起被角,查看我的伤口。
“那么长的剑刺进去,阿清该多疼啊,她最怕疼了。”
是啊,我最怕疼了。
小时候,我背书不认真,爹爹就折下柳枝,作势要打我。
软绵绵的柳枝,打起人来一点都不疼。
但娘还是把我护在身后,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的阿清,就算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。”
可也是这么护我宠我的娘,狠狠扇过我一巴掌,让我半张脸肿了半个月。
我素来最爱侍弄花草,清光苑被我种满了各色各样的花。
有次,我在街上遇到几个西域行商,他们兜售的花种,我从未见过。
我买下两株,一株种在偏院,一株送去清光苑。
我并不是要讨好莫宛溪,只是觉得,百花盛开的清光苑应该有这样一株花。
当天晚上,我睡得正香,便被两个粗使嬷嬷拖下了床。
我什么都不知道,就被一路拖行到清光苑。
我娘见了我,二话不说给了我一巴掌。
力道好大,半边脸都肿了起来。
我被打懵了,耳鸣目眩的,半天才缓过神来。
这是我娘第一次打我。
她用看仇人的眼神看我:“莫清,你知不知错?”
我呆呆看着她:“我怎么了?”
天地良心,我当时真的完全不知情。
那两个嬷嬷拖死猪一样把我拖过来,我问她俩要带我去哪儿,要做什么,她俩也不回答。
我一过来,人还没站稳就挨了一巴掌,我觉得天底下没有比我更冤的人。
我娘眼神冰冷:“你白日里送了什么毒花过来?害得宛溪起了一身的风疹,现在还昏迷不醒。”
我微微一怔,随即释然苦笑。
我当她是为了什么事如此大动干戈,原来又是为了莫宛溪。
我脸上火辣辣的疼,心底却一阵寒凉。
她甚至都没问我,就先给我定了罪。
我拭去嘴角血迹,不紧不慢道:“不管您信不信,我从未想过加害莫宛溪,以前不曾,以后更不会,我如今只想守着偏院,种种花,除除草,仅此而已。”
“至于我白天送去的花,也不是什么毒花,只是西域泊来的品种,我见了觉得新奇所以才往清光苑送了一株。”
我爹半信半疑:“莫清,你当真不知?”
有时我真的好疑惑,既然他们不相信我,又何必问我呢,直接定罪处决我多好,省时省力。
我也不用在这过程中备受煎熬。
其实我早该习惯,却还是忍不住委屈:“我为什么要撒谎?”
我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:“骨子里的劣根性,是改不了的。”
他话里的意思已经很直白了。
当初我亲娘因为嫉妒,调换了我和莫宛溪。
所以我也会因为嫉妒,害得莫宛溪起风疹。
哪怕这不是我的错,也是我的错。
我亲娘是罪人,所以我也是罪人。
那时我就已经在想,若是有天我死了呢,他们还能把气往谁身上撒?
莫宛溪回来后,爹娘防我像防贼似的。
我永远在辩解,但永远没人信。
我差点就要脱口而出,承认这是我干的了。
总归我做什么都是错。
认了便是。
打都已经挨了,总不能白挨。
反正他们扣在我头上的罪名也不是一两项了,在他们眼中,我就是鸠占鹊巢的坏种,心怀鬼胎的小人,不得好死的败类。
我刚想开口。
一个大夫慌慌张张从屋里跑出来,终止了我们的暗流涌动。
“老夫仔细查验过了,令爱风疹昏迷的因由,不在那株西域花上,而是令爱午时食用的一碗虾羹,令爱的体质,不宜食用含虾的食物,否则便会风疹昏迷,往后膳食,还请多加注意。”
我娘愣了好一会儿,神情复杂地看向我,伸手想碰我肿得老高的脸。
我往后退了一步,躲开了。
“既然真相大白,没我什么事,我就先走了,不在这里碍你们的眼。”
我承认,最后半句话,带了些赌气的成分。
我以为,知道这是一场误会后,爹娘就算不会向我道歉,至少也会哄哄我。
但是并没有。
我还没走远,爹娘就已经围住了大夫,询问莫宛溪的身体状况。
无人在意我。
我故作轻松地转过头,潇洒地哼着不成曲的小调,回到偏院,挖出树下埋的桃花酒,对月独酌。
没关系的,至少还有月亮陪我。
没有谁的爱是永恒的,但月亮是永恒的。
十三年的爱会忽然消失,但月亮不会,无论再过多少年,月亮还是月亮。
6
我这口气吊了好久,上不去下不来,活不了死不成。
我的灵魂便只能困在屋里,百无聊赖地看着他们来了又去。
莫宛溪到底年龄小,守不住寂寞,总是见不到她人影。
爹娘倒是守在我床边,一刻也不敢离开。
爹说:“阿清还记得吗,小时候你怕黑,爹娘就是这样守着你睡的。
我当然记得,那时候我被养得多娇气啊。
可我现在已经不怕黑了,也不需要人守着我睡觉了。
在偏院那一年,我每个夜晚都是自己哄着自己入睡。
在贫民窟这一年,我已经修炼到了更高的境界,就算有老鼠蟑螂从我脸上爬过去,我都能面不改色地翻身继续睡。
被抛弃和遗忘的人,总得慢慢适应孤独。
清晨,莫宛溪捧了一束丁香花进来,放在我枕边。
“莫清,你最喜欢花,就让这束花陪着你吧。”
我娘看见花束,又情不自禁流下眼泪:“阿清,春天快到了,你十岁那年种的藤藤花,已经爬满了秋千架,等你醒过来,娘再推你荡秋千。”
原来娘还记得我喜欢春天。
我出生在春天,所以娘为我取名清字
春天的清光苑会变成一个芬芳的大花园,娘推着我荡秋千,我飞得好高好高,风里全是春天的味道。
可惜清光美好,却总是易逝。
清光苑早就不属于我了
我也等不到明年立春了。
就连莫清这个名字,原本也不是我的,而是属于莫宛溪的。
所以离开京城后,我就给自己改了个名字。
叫阿苕。
我本该是颗野草,不该因为恰好生在春天,就贪恋那点清光。
爹说不敢对我好,是因为怕莫宛溪难受。
娘说对我冷淡,是因为心疼莫宛溪。
他们都爱莫宛溪,余下来的爱,才会分给我。
这本是理所应当的,可我还是好嫉妒。
爹说我改不掉骨子里的劣根性。
其实也没说错。
我嫉妒莫宛溪。
可她的确是个很美好的人,把我的嫉妒都衬托得卑劣不堪。
她这次来忻州,是为了祭拜莫春娘。
莫春娘害她过了那么多苦日子,她却一点也不恨,还特意来祭拜。
她的世界充满了爱和美好。
难怪所有人都爱她。
不像我,我心里有好多好多恨。
可我谁也不能恨,只能恨我自己。
莫宛溪在贫民窟吃了十三年的苦,所以我也把自己扔进贫民窟。
夏日酷暑,冬日寒凉,雨打风吹我都受着。
贫民窟的人,生病了是没钱去医馆的,只能靠自己扛,扛过去了就生,扛不过去就死,在这里,生死都是很平常的事。
烧得迷迷糊糊时,我忍不住想,从前我真是轻看莫宛溪了,她可不是娇弱不堪的小白菊,她是生长在峭壁上,雨打风吹也不倒的岩花。
莫宛溪曾流落青楼,我本想把自己卖身青楼,但青楼的妈妈对我很是嫌弃。
一来是那时我太瘦弱,二来是因为我不会弹琴。
忻州的阿苕是不会弹琴的,但京城人人都知道,莫家阿清琴艺炉火纯青。
可惜,我再也无法弹琴了,因为我的右手废了。
这是个谁也不知道的秘密。
连我哥都不知道。
嘘,这个秘密,会被我带进棺材里。
7
作为莫家千金,我实在太平庸。
虽然娘总说,我什么都不会也没关系。
但我明白,她只是因为爱我,所以才接受我的平庸。
诗词歌赋,琴棋书画,我只精通一个琴。
我好吃懒做,唯独在琴艺上苦心孤诣,废寝忘食,只是因为,我娘无心的一句夸赞。
她说:“阿清这双手,生来便是抚琴的。”
可我这双被娘夸赞过的手,再也无法抚琴了。
莫宛溪风疹昏迷醒来后,得知我被误解,还被掌掴,好心来偏院探望我。
她红着眼向我道歉:“莫清,此事皆是因我而起,是我不想浪费娘的心意,以为少吃一些没关系,都怪我身子不中用,却害得你被冤枉。”
我把头闷进被子里,懒得理会她。
该道歉的人不来道歉,她上赶着道哪门子歉。
这事我怎么也怪不到她头上啊。
没想到她居然上手扯我被子:“莫清,你这样会闷坏你自己的,我听说你好几天没吃东西了,我给你带了好吃的,你起来吃点吧。”
我不耐烦,反手把她推开。
我没想到她那么瘦弱,我只是轻轻一推,她就跌倒在地,脑袋撞到了桌角。
于是她刚清醒没几天,又陷入了昏迷。
爹娘很生气,罚我去跪祠堂,莫宛溪一天不醒,我就一天不许起来。
我心里也很愧疚。
我跪在祠堂,祈求莫家列祖列宗保佑莫宛溪,希望她快点好起来。
为显诚意,还抄写了好几卷经书。
哥哥知道我推了莫宛溪后,怒气冲冲跑到祠堂。
他一把将我拎起来:“哪只手推的?”
我最开始没反应过来。
直到他将我狠狠摔倒在地,我才明白,他是来兴师问罪的。
我在祠堂跪了三天,滴水未进,连说话都没力气。
不过,我的经验告诉我,解不解释都是一样的结果,他们只相信他们认定的。
他发狠地咬牙:“不说是吗?那我就当是右手了。”
他不由分说,一脚踩上我的右手背,力道之重,像是恨不得把我的手碾碎。
“疼吗?你有没有想过,宛溪也会疼?”
我当然疼。
可我连叫喊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
真的好疼,火辣辣的刺痛传遍全身,疼得我整张脸都跟着抽搐痉挛,冷汗进发。
直到我半边身体都麻木,失去知觉,像死鱼一样蜷缩在地板上,莫昭才收回脚。
他目光瞥见我抄好的经书。
神情怔忪了一瞬,但也只是一瞬,便又化作满脸冷嘲。
“你在这里假惺惺地装给谁看,宛溪要是醒不过来,你就在这里跪一辈子吧。”
他毫不留情地撕碎了我抄了三天的经书,扔进了火盆里,再也没看我一眼,转身离开。
我没有假惺惺,也没有要装给谁看。
我是真心实意希望莫宛溪快好起来。
8
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,也不知睡了多久。
再清醒时,我发现我的右手已经没有知觉了。
我还没来得及接受这个事实,两个五大三粗的嬷嬷就又把我拖出了祠堂。
莫昭废了我的右手还不解气,他要把我赶出莫家
他说我心术不正,先是害得莫宛溪起了风疹,现在又害得莫宛溪撞到头,留我在莫府,迟早是个祸患。
反倒是娘动了恻隐之心。
娘深深看了我一眼:“算了,我也不忍心让这孩子自生自灭,就把她送到庄子上去吧。”
可我不想去庄子。
庄子上都是被罚役的下人,戒备森严,进去了兴许这辈子都出不来了。
我才不想被关在那里一辈子直到老死。
于是我在半道跳车逃了,来到了忻州。
这里是一切变故的转折点,是我和莫宛溪命运颠覆的开始。
从这里开始,那就从这里结束,也算有始有终。
大概只有这样,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
我没想到,莫昭会追到忻州来。
我不知道他到底跟了我多久。
在我被第十七家青楼拒之门外后,他终于忍不住现身了。
他咬牙切齿地瞪着我:“莫清,你到底要自甘堕落到什么时候?”
我奇怪地看着他,没说话。
他不是要把我赶出莫家吗?我自甘堕落与他又有何干系?
莫名其妙。
我不搭理他,他却越说越起劲。
一会儿气急败坏地骂我,说我下贱,败坏莫家名声。
一会儿又低声下气的,说我变了,变得好陌生,说我们之间不该是这样。
无论他说什么,我都只安安静静地看着他。
他有些慌了。
兴许是他从没见过这么安静的莫清吧。
其实,他从前对我的疼爱不比爹娘少。
我爱玩爱闹,总是惹祸,每次都是莫昭给我兜底。
爹娘舍不得教训我,揍起莫昭来却不手软。
他挨揍后,我就偷偷跑去看他,问他疼不疼。
他笑嘻嘻地说:“阿清呼呼,哥哥就不疼了。”
春风最盛的时节,我会约上京中贵女去放纸鸢。
哥哥亲手给我扎的纸鸢,一定是飞得最高的。
后来他成了莫宛溪的哥哥,再没对我笑过,也再没给我扎过纸鸢。
他只会踩着我的手,问我有没有想过宛溪也会疼。
莫宛溪的右手,磕到碰到一定会疼,但我的右手再也感受不到疼了。
莫昭一路跟着我回到贫民窟,看见我住的地方破烂不堪,眉头一皱:“你就住在这种地方?”
我忍不住说:“莫宛溪也住过这种地方。”
他便不说话了。
过了好久,他才语气不善地问:“莫清,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
这次我没再回应他。
他不知搭错了哪根筋,开始发疯,砸我屋里的东西。
我就静静看着他,等他砸够了,再默默上前收拾。
他用极其受伤的眼神看着我:“莫清,你的心真硬。”
我觉得他好可笑。
从头到尾,他都没发现我的右手已经废了
却说我的心硬。
难道他的心软吗?
他踩断我的手时,心软过吗?
9
我猜莫昭迟迟不现身,是因为没脸见我。
因为大夫说完,我还剩最后三个时辰后,他就出现了。
莫宛溪在我床前泪流满面,泣不成声。
我想替她擦眼泪,手却穿透了她的脸庞。
我垂眸看着自己透明的双手。
说不清心底是什么感觉。
释然、遗憾、冷静、轻松。
我没有带着恨意离开,我不恨任何人,也原谅所有人。
在长剑刺穿我胸口的那一刻,我所有的痛苦就夏然而止了,我身为莫清,这草十五年的短暂一生,就结束在这里。
莫昭从怀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纸,颤抖着手捧到我面前。
“阿清,哥哥抄了三天三夜的佛经,为你祈福,希望你来生别再遇到我这样糟糕的哥哥。”
当初,我为莫宛溪祈福时抄的佛经,被他撕碎了扔进火盆里,当着莫家列祖列宗的面烧成了灰烬。
他说我假惺惺,装样子。
哥哥,你如今又有几分真心?
莫宛溪忍不住问道:“她活着时,你们为什么不对她好一点?”
她的话一针见血。
所有人都沉默了。
我爹痛苦地锤着胸口:“我错了,大错特错,错得离谱啊!”
我娘失声痛哭,悲切到了极点,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我哥沉默许久,忽然抬手猛扇自己巴掌:“我是个混蛋,该死的人是我!“
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始讨伐自己。
我只觉得吵闹。
莫宛溪叹了口气,将我从床上抱了起来。
那么瘦弱的她,抱着我,步子走得缓慢却坚定。
我想问她,要带我去哪儿。
她仿佛能听见我的心声似的,轻声说道:“我带你去一个开满花的地方,你的长眠之地,应该花团锦簇。”
她顿了顿,又说道:“莫清,我从来没有怨过你,也不觉得你亏欠我,若有来生..”
算了,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
我想说,莫宛溪,我也从来没有怪过你。
我的灵魂在阳光下慢慢变得透明。
我在世上仅存的一丝意识渐渐模糊。
莫宛溪,不要为我难过。
清光苑的花快要开了,如果想念我,就多替我看看春天。
【莫宛溪番外:见春天】
1
四岁那年,我就知道我娘不是我娘。
我娘得了肺病,整日整夜咳血,总觉得自己第二天就会死。
所以她每天都要拉着我,进行一次忏悔。
“宛溪,我对不起你,你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,我却把你偷走,让你跟着我过苦日子,我真不是东西。”
“宛溪,等我死了,你就去找你的亲生爹娘吧,你去京城,找莫府,京城最大的莫府,那家的老爷夫人,就是你的亲生爹娘。”
“宛溪,你要怪就怪我,别怪我那可怜的孩子,她是无辜的,是我一时鬼迷心窍,酿成大错,我无数次想带你回到莫府,坦白这段过往,可我实在不敢。”
诸如此类的话,每天一遍,我对我的身世已经倒背如流。
其实我根本不在意。
我是莫宛溪还是莫清,是富家千金还是贫民窟的小乞丐,又有什么关系呢?
人干嘛非要活在规矩和关系里?
我只知道,我跟这个叫莫春娘的女人生活了五年,我管她叫娘。
如果没有她,我早就饿死了。
贫民窟有贫民窟的生存法则,女人和小孩,在这里是最弱势最低端的存在。
在这里,每一口吃的,都是从别人嘴边抢过来的。
假如她把我当累赘,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活到五岁。
我俩谁也不是谁的拖累,而是彼此的依靠。
所以我真的不恨她。
也不恨莫清。
我知道我的身世,但我没想去京城认亲。
因为我娘临死前说:“我在人世间只有两个牵挂,一个是你,另一个就是我的亲生女儿,等我死后,你便去京城认亲吧,到时候,请你给我那无辜的女儿谋个好出路。”
我实在想不出,能给她谋个什么好出路。
想来想去,让她继续做好莫家千金,就是最好的出路了。
于是,安葬我娘后,我留在了忻州,开始了我摸爬滚打的人生路。
我真没觉得有多苦,反而觉得挺有意思。
人生苦短,无趣的事太多,有趣的事太少。
与其在深闺里做大小姐,还不如让我好好探索一下这偌大的人世间。
我没想到,人间险恶,我一个小毛丫头,独自闯荡江湖,风险还是太大。
我差点折在醉春楼。
还好遇见一位高手,路见不平,拔刀相助,救我于水火之中。
我还没来得及言谢,就晕了过去。
没想到再醒来时,我已身在京城。
哦,真是糟糕。
原来那位高手,就是我血缘上的亲哥哥。
我打死也没想到,兜兜转转,我还是回到了莫家。
我抬头,看向我亲娘身后那个雪肤乌发的少女。
莫清,我们终于见面了。
2
很小的时候,我娘就说,我天生会演戏。
到了莫家后,我尽心尽力扮演着小白花的角色,并且很快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。
尤其是在莫清面前。
我娘是个美人胚子,所以莫清也很漂亮。
莫清很喜欢花。
如果要用一种花来形容她,我觉得应该是丁香,美丽,忧愁。
而我的存在,似乎就是她最大的忧愁。
我想帮她摆平一些麻烦,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
比如敲点敲点厨房和库房那帮眼高手低的家伙。
上次见她时,我听见她在咳嗽。
一声声咳得我心都在颤抖。
我娘死之前,也这样一直咳。
我很害怕,我怕莫清像我娘一样。
我把给莫清的碳全都换成了无烟碳。
我希望她好好的。
但我完全无法说服我的家人。
他们就跟入了魔怔似的。
我不是没对他们说过,我说我不怪莫清,希望他们能对莫清好点。
他们只会欣慰地摸摸我的头,夸我是个好孩子,转眼继续对莫清冷眼相加。
那段时间我身体虚弱,顾得上这头,便顾不上那头。
后来我才知道,莫清受了很多委屈。
都怪醉春楼那帮杂碎,害我体质变弱,无法保护她。
最让我无能为力的一次,是我在偏院撞到头晕倒后那次。
我从昏迷中苏醒,便得知,莫清被送去了庄子上。
我赶紧去找我亲娘,想向她打听,莫清到底在哪个庄子,我好偷偷去看她。
没想到,正好遇上几个车夫惶恐地回话,说莫清跳车跑了。
我心跳猛地漏了一拍。
跑了?
她会去哪里?
她能照顾好自己吗?
我亲娘神情有些哀伤,许久才道:“也罢,跑了便跑了吧。”
我忍不住问道:“不找找吗?”
她摇摇头:“不必。”
我有些难过。
替莫清难过。
没关系,他们不把你当家人,我把你当家人。
莫清,我们还会见面的,对吗?
3
我没想到,我会在忻州遇见莫清。
是啊,我想过一切可能,怎么就没想到莫清会在忻州呢?
我是在祭拜我娘时遇见莫清的。
那天是我娘的忌日。
我从东去,她从西来,我俩就这样奇迹般地相遇了。
她瘦了很多,也憔悴了很多。
我以为她会照顾好自己,可她并没有。
我有些心疼。
要是我能早点找到她就好了。
我带她回我在忻州的住处。
刺客就是这时出现的。
他们明显是冲我来的。
我那时没想到莫清已经绝望到一心求死的地步,我以为我们还有很多时间。
所以,我根本没注意到,莫清眼中闪过的一抹决绝。
待我反应过来时,她已经浑身是血倒在了地上。
我头一次知道,人可以那么慌张,慌张得全身都在颤抖。
可我顾不上慌张,我咬紧牙关,背着她往城里跑,去找城里最好的大夫。
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。
我不能让她有事,绝不能。
快到医馆时,莫清勾着我的脖子,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:“莫宛溪,这条命还你往后,我再也不欠你了。”
….莫詔。
你是笨蛋吗?谁要你的命?
你本来就不欠我什么。
莫清,你不能有事。
莫清,活下去,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我,就活下去,以后慢慢偿还我啊。
还我一条命,到底算什么啊…
大夫说,她没救了。
我不懂,为什么会这样?
我刚才还在为我们的重逢而喜悦,为什么命运要这样安排?
莫家的人来得很快,我冷眼看着他们忏悔、自责,心想,你们早干嘛去了?
如果不是他们,让莫清心灰意冷,逼走了她,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?
更可恨的是,他们每个人都打着为我好的旗号,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听我说话?
我说了,我不恨莫清,我不讨厌莫清,我不怪莫清。
我
很想保护莫清。
但我没做到。
那天我背着所有人,喝得烂醉如泥。
我抱着一棵树,喃喃自语说了好多。
一会儿把树当成我娘,一会儿把树当成莫清。
“娘,对不起啊,我没有照顾好她。”
“莫清,你这个自作主张的混蛋,你给我回来。”
"娘,你见到莫清了吗?我再也见不到莫清了。”
“莫清,你最喜欢什么花?我最喜欢丁香”
我将莫清安葬在一个山清水秀、花团锦簇的秀丽之地。
只有我知道她在哪里。
莫家人先后来问我,但我谁也没说,那里很安静,我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。
回到京城后,我和爹娘审问了落网的刺客。
严刑逼供下,刺客全都交代了。
他们是我亲爹的政敌派来的。
我亲爹越发悔恨。
很好,就让他们在悔恨中度过一辈子吧。
我亲爹问我,刺客该怎么处理。
我情绪很激动,手指紧紧捏着桌角,咬牙道:“凌、迟!我要他不得好死!”
我亲爹似乎被这样的我吓到了。
我缓和了情绪,露出一个微笑,转身离开了地牢。
我回到清光苑,靠在爬满藤藤花的秋千架上。
闭上眼,仿佛能看见莫清坐在秋千上的场景。
这里的一草一木,一花一树,我都没有动过。
春天到了,清光苑的花都开了。
莫清,你看见了吗?
(全文完)
-
Burberry 北京三里屯旗舰店盛大揭幕
2025-07-06 -
打造多样课程体系 赋能孩子兴趣发展:云南昌乐实验中学举行“半天活动课程成果集中展示活动”
2025-12-29 -
清岛湾78平毛坯东侧大海万亩黑松林西侧绿岛湖
2025-01-20 -
房产早报丨成都东安新城迎变局:华侨城月内两度出手,揽地超300亩
2025-08-20